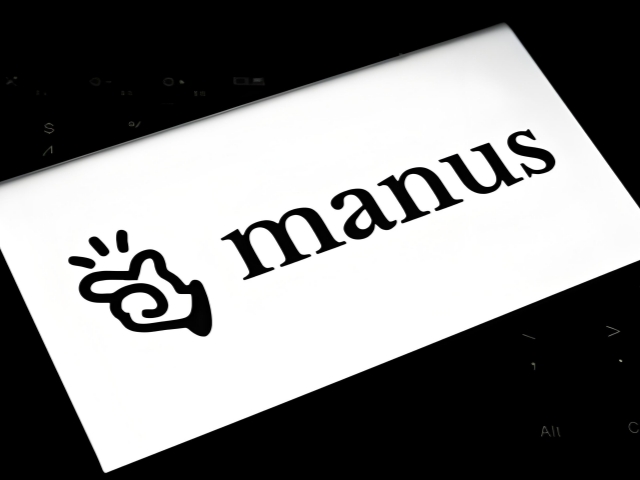在中国经济这盘大棋里,有些变化是锣鼓喧天的——比如万亿刺激、楼市狂飙;而有些转折却悄无声息,只在制度深处轻轻拨动一根弦,却可能改写整个游戏规则。
最近,财政部低调设立了一个新部门:债务管理司,统一负责政府债务的额度分配、发行和偿还。乍看只是机构微调,但若放在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运行的脉络中细看,便会察觉:那个靠土地做抵押、层层加杠杆撑起增长的时代,正在缓缓退场;而一个以科技、数据和创新为信用基础的新循环,正悄然铺开。
回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推出4万亿元刺激计划,把增长引擎从出口切换到投资。此后十余年,中国经济仿佛被装上了一台“债务—投资”联动的马达。
先是地方政府通过城投平台大举举债,修路架桥、建厂扩产;接着是居民加杠杆买房,房地产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到了2020年以后,中央政府接过接力棒,推动新能源、半导体、高端制造等领域的投资。这三个阶段,不仅对应不同的产业重心,也映射出债务主体的轮动——从地方,到家庭,再到中央。

而贯穿这一切的,是一块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抵押品”:土地。由于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地方政府既能低价供地招商引资,也能高价卖地换取财政收入,还能把土地注入城投公司作为融资担保。
这种机制形成了一套自我强化的闭环:卖地收入支撑基建投入,基建提升区域价值进而推高地价,地价上涨又反过来支撑更多融资。老百姓看在眼里,自然相信“房价只涨不跌”,于是纷纷贷款买房;开发商则在中间穿针引线,把土地价值变现,并带动钢铁、水泥、家电等一整条产业链同步运转。
这套模式在过去十多年高效运转,但也逐渐显露出疲态。自2020年起,房地产市场降温、人口结构变化、地方财政承压,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滑。许多城投平台陷入“借新还旧”的困境,债务风险开始浮出水面。
中央随即出手,不再简单“去杠杆”,而是转向“控新增、化存量、调结构”——核心是切断地方政府通过隐性渠道无限加杠杆的路径。由于大量存量债务高度依赖滚动融资,一旦新增闸门收紧,整个链条便迅速减速。过去两年,家庭杠杆几乎停滞,企业加杠杆的速度也明显慢于政府,传统债务驱动模式已难以为继。
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债务管理司的设立显得意味深长。外界普遍认为,它的首要任务是严控地方新增隐性债务,尤其是那些打着“城市更新”“产业园区”旗号的传统基建项目。但更深层的意图,或许在于引导一场结构性转型:债务扩张并未停止,只是换了跑道——从依赖土地抵押,转向依托科技资产、数据要素、知识产权等新型信用载体。
已有不少地方开始尝试这种转换。一些城投公司手中握有大量闲置或低效的工业厂房,过去这类资产因缺乏现金流而难以处置,甚至成为负担。如今,不少地方政府主动引入科技企业入驻,将旧厂房改造为研发中心、智能制造基地或数字经济园区。这些空间虽然不再靠“卖地”赚钱,却因其承载的技术活动、产业集聚效应和未来收益预期,逐渐被银行和资本市场视为可接受的融资基础。部分地方已开始以此类资产为基础申请贷款或发行专项债,所筹资金既可用于化解历史债务,也可继续投入创新生态建设。
这也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明明财政吃紧、整体经济增速放缓,地方政府为何仍对高科技制造保持如此高的投资热情?数据显示,高技术产业投资近年来持续保持约10%的年增长率,远高于固定资产投资整体水平。这背后,既有国家战略的牵引,也反映出地方在土地财政退潮后,试图通过培育新质生产力来重建可持续财源的努力。
在这个过程中,新设的债务管理部门或将扮演双重角色:一边堵住传统债务的漏洞,防止风险再度积聚;一边搭建制度桥梁,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有序流动。毕竟,给一块地估值容易,给一项技术、一个算法或一个研发团队定价却复杂得多。相较于土地这一标准化、同质化、国有主导的要素,科技与创新更具多样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也更有利于民营企业参与。这种转变若能稳步推进,不仅有助于化解债务风险,还可能重塑中国经济的微观活力。
当然,这场转型才刚刚起步。科技创新资产的估值体系尚不成熟,知识产权保护、数据确权、未来收益权质押等配套机制仍在探索中。正如塔勒布在《反脆弱》中所说:“风会熄灭蜡烛,却能使火焰越烧越旺。”中国的债务模式能否借这股东风完成从“土地信用”向“科技信用”的跃迁,不仅关系到财政安全,更将决定未来增长的质量与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