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的阿里园区里,一个戴着工牌的身影时常出现在会议室外的走廊上。他不主持会议,也不签发文件,但他的出现本身,已足以让管理层重新评估某些决策的优先级。这个人是马云。自2020年蚂蚁集团IPO被叫停后,他从公众视野中淡出,五年间,关于他的消息多与海外行程或私人生活相关。如今,他频繁现身阿里巴巴各业务部门,尤其在云业务和电商前线,与高管交流技术进展,关注补贴策略,甚至一天内多次追问项目细节。尽管没有正式头衔,但多方信息显示,他在公司事务中的参与程度,已达到近五年来的最高水平。
这种回归,首先引发的不是组织结构的变化,而是心理层面的震动。在张勇执掌阿里巴巴的数年中,公司尝试通过组织裂变——将集团拆分为六个独立业务单元——来激发活力,并推动各板块独立融资或上市。然而,资本市场波动使得多数IPO计划搁浅,各业务在战略上也逐渐显现出协同不足、资源分散的迹象。与此同时,拼多多在下沉市场的持续渗透,美团在外卖与本地生活领域的巩固,使得阿里的核心电商业务面临份额流失的压力。高盛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7月,美团在中国外卖市场占据47%份额,阿里虽以43%紧随其后,但追赶过程仍显吃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创始人的“在场感”成为一种稳定预期的象征。
马云并未直接接管管理权,而是通过影响蔡崇信、吴泳铭和蒋凡等核心管理层,间接参与战略决策。蔡崇信作为董事会主席,长期被视为马云在治理层面的代言人;吴泳铭则凭借技术背景,被委以主导公司向人工智能转型的重任;蒋凡曾是马云亲自指导的少数高管之一,经历个人风波后重新被启用,如今负责整合淘宝、外卖与物流等电商业务。这一组合,既保留了职业经理人的执行框架,又嵌入了创始人信任网络的关键节点。这种安排,使得战略方向的调整既能保持组织稳定性,又能快速响应市场变化。
值得关注的是,马云的介入重点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人工智能,二是核心电商的市场争夺。阿里巴巴已宣布未来三年将投入超过3800亿元用于AI和云基础设施建设。2025年第二季度,阿里云收入同比增长26%,创下多年来的最快增速。这一成绩背后,是公司对通义千问大模型、平头哥芯片等自研技术的持续投入。据知情人士透露,马云几乎每天都会收到相关进展汇报,并在内部会议中强调技术对长期竞争力的意义。他在一次云业务活动上提到:“技术不仅仅是为了征服星辰大海,更是为了守护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火花。”这句话被记录在案,虽带有个人色彩,但也传递出对技术价值的重新定位。
在电商领域,他的影响更为直接。面对京东在特定品类的突袭式进入,阿里巴巴决定投入高达500亿元人民币进行用户补贴,以巩固市场份额。这一决策的背后,有马云的推动。尽管公司未公开其具体角色,但熟悉内情的人士指出,他在关键讨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大规模补贴策略,虽在短期内有效遏制了竞争对手的扩张,但也引发了外界对“价格战”是否可持续的讨论。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做法与监管层近年来对“恶性竞争”和“不当补贴”的警惕形成潜在张力。马云曾在2020年因公开批评金融体系而引发监管反应,如今他在市场策略上的强势介入,是否会再次引发政策关注,仍是未知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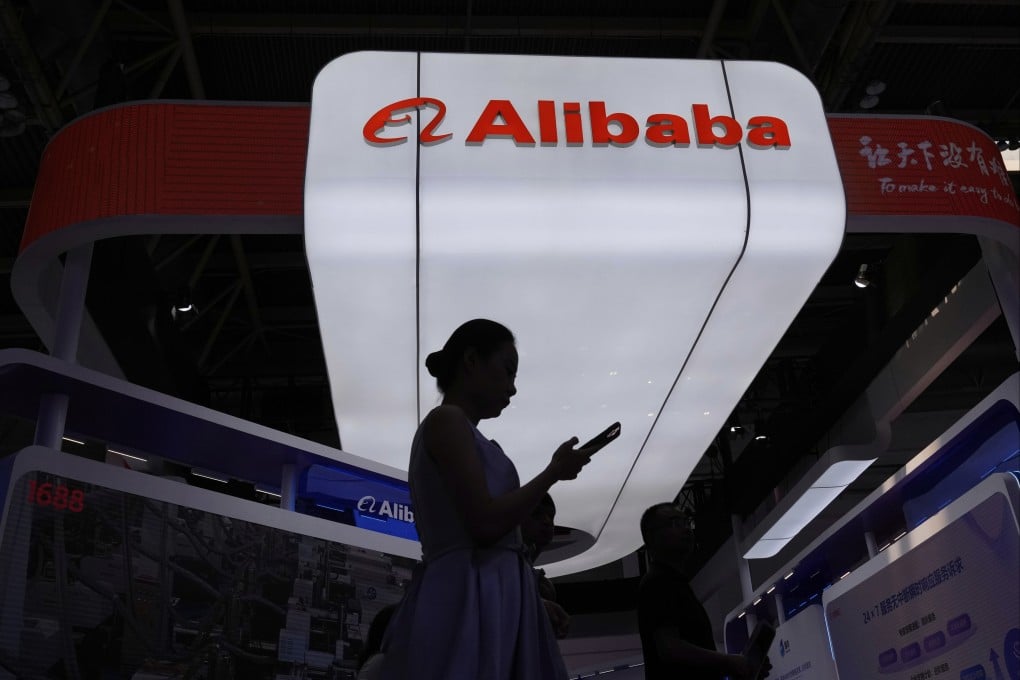
他的回归方式本身也值得玩味。他没有重返董事会,也未担任任何管理职务,而是以“创始人”身份参与关键讨论。他佩戴工牌、出现在园区,被员工解读为一种象征性姿态——表明他与公司重新建立日常联系。这种非正式的影响力运作,既避免了权力结构的剧烈变动,又能在关键时刻施加引导。对于员工而言,他的出现唤起了对早期创业文化的记忆。2025年4月,他在阿里云总部走过贴满老员工留言的走廊,听他们讲述公司低谷期的困境,现场气氛被描述为“像初创公司第一天”。这种情感连接,虽难以量化,但在组织士气低迷的时期,具有实际意义。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马云的回归,反映了中国头部科技企业在经历监管调整与战略试错后,对“创始人权威”的重新依赖。在职业化管理未能完全兑现增长预期的情况下,创始人的战略直觉与文化影响力,成为组织纠错的重要资源。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司治理将重回“人治”模式。相反,他的角色更像一个“战略校准器”——在重大方向上提供判断,在关键人事上施加影响,但不介入日常运营。这种模式,既保留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框架,又嵌入了创始人特有的判断力。
当然,这种非正式权威也带来挑战。他的存在可能使汇报关系变得模糊,部分员工倾向于将他视为最终决策者,从而影响正常管理流程。此外,他对补贴战的支持,虽在战术上有效,但在长期竞争与合规层面仍存争议。他的每一次公开露面或内部发声,都会被市场与监管机构重新解读,这种关注度本身,就是一种风险。
马云的归来,不是一场戏剧性的复辟,而是一次静默的渗透。他不再站在舞台中央,却依然能影响灯光的方向。他试图推动的,不是对过去的简单复制,而是在新的约束条件下,重建阿里的战略聚焦与组织信心。至于这种模式能否真正“让阿里巴巴再次伟大”,时间会给出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他的回归,已让这家公司的空气,变得不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