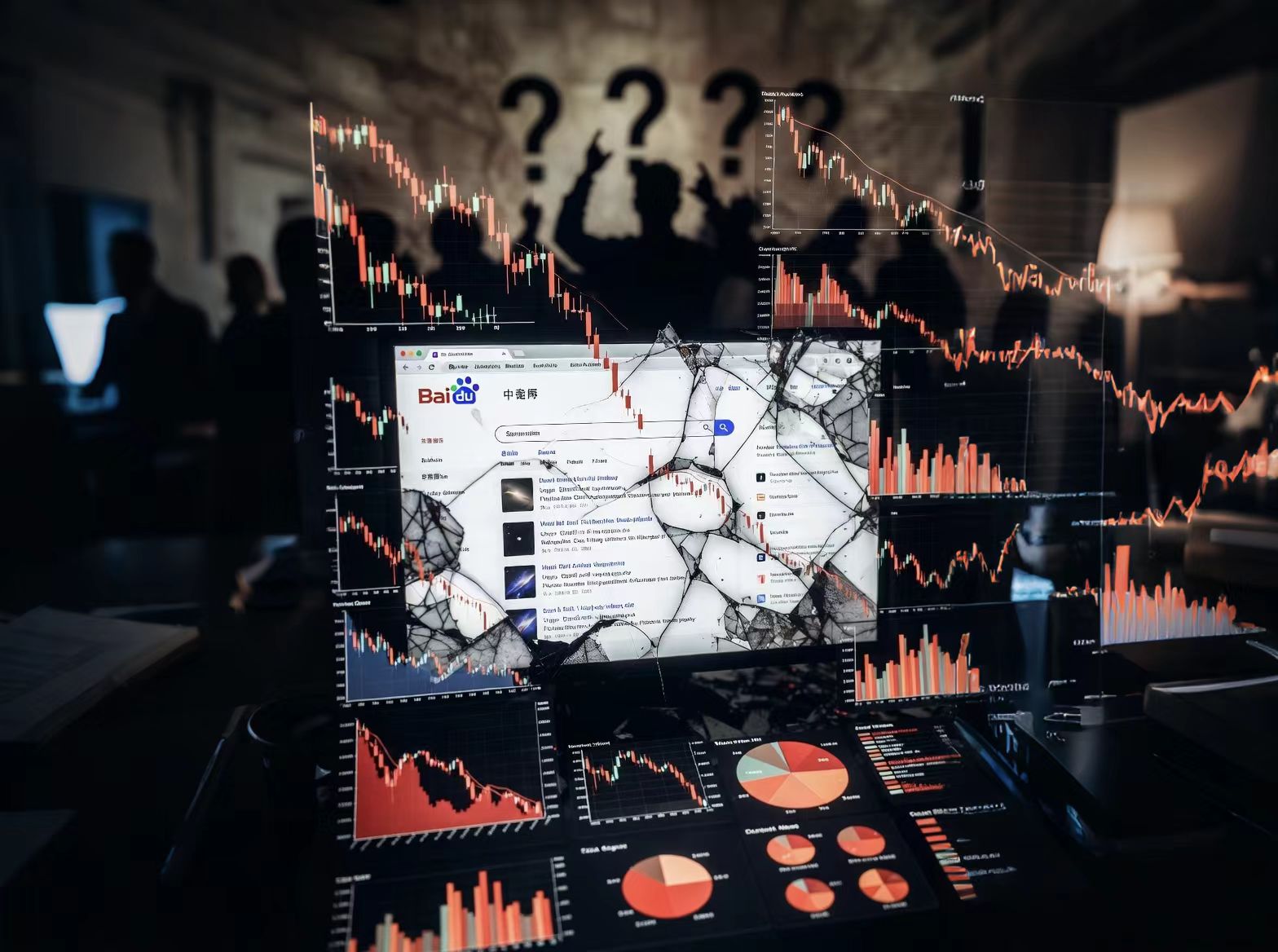在日本,我们经常看到头发花白的老人家开出租车来维持生计,有些七十多岁、甚至快八十岁的长辈还在居酒屋打工挣钱。还有一些老人,尤其是女性,因为孤独、贫穷和缺乏社会支持,居然故意去商店「零元购」,然后自首,只为了进监狱度过余生。
其实不只日本这样,作为福利国家之一、社会保障制度先驱的德国,也面临类似的困境。根据德国养老金保险数据,61%的养老金领取者每月净额不足1200欧元,根本不够支付住房、医疗和生活开销。
政府数据显示,2023年约有1770万德国人(占人口21.2%)处于贫穷边缘,很多老人得靠社会援助过日子。大约20%的欧洲老人(包括德国)面临退休贫穷风险,而德国的老人贫穷率甚至高于欧盟平均水平。
德国的养老金体系(主要靠法定养老金)存在明显的不足。老龄化社会、性别差距、生活成本上涨,以及养老金水平跟不上时代,导致许多老人陷入贫穷风险。
德国政府试图透过提高退休年龄(目前是67岁,有人建议延到70岁)或引入私人养老金来应对危机。OECD和德国央行警告,如果不改革,这套体系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养老金水平可能继续下降,或是缴费率得升到24%以上。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本世纪初,大家常说西方福利制度多么优越,能移民到德国或日本、入籍那里就等于人生巅峰。但如今再看,这些国家的政府债务深陷泥沼,福利体系摇摇欲坠。回溯历史,19世纪70年代,德国工业化带来工人阶级的贫穷和不满,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潮如潮水般涌现。
为了收买工人、削弱左派社民党的吸引力,德国铁血首相奥托·冯·俾斯麦转向讨好民众的「胡萝卜」政策:透过国家社会保障满足工人部分需求,让他们忠于帝国而非革命。俾斯麦曾直言,这些改革是为了「从社会主义者手中夺走武器」,防止激进变革。
1881年,俾斯麦开始推动社会立法。
1883年:疾病保险法,强制工人和雇主缴费,提供医疗和病假工资。
1884年:实施事故保险法,涵盖工作事故。
1889年:养老和残疾保险法,引入养老金系统。
是不是有点熟悉?这不就是我们的医疗险、工伤险、养老金吗?再加个失业险和公积金,就成了四险一金。
没错,这是全球最早、最雏形的社会保险制度。想不到吧,居然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搞起来的。
你可能会问,德国政府突然增加这么多福利支出,钱从哪来?比如,怎么给现在的老人付养老金?俾斯麦的制度是现收现付、强制保险。让现在的年轻人给老人养老买单,先解决眼前问题再说。
当时的保守派和经济界就质疑这套制度的长期可持续性,他们指出,如果依赖年轻一代缴费,一旦出生率下降或经济衰退,以后怎么办?就像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后来所说:「政府干预经济,总是会制造出更多问题,需要更多干预来修补。」
其实,他们也想过养老金破产的风险,所以把退休年龄设为70岁。那时德国人的预期寿命低(男性约45岁),大部分人根本活不到领取养老金的年纪,池子里的钱自然越积越多。
这些政策大大缓和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德国模式很快影响邻国:奥地利、瑞士、北欧国家,,连大英帝国后来也抄作业。
在这之前,各国的医疗、养老主要靠家庭、社区、宗教组织或地方互助,而不是中央政府主导的全面保险体系。德国为国家包揽家庭的责任开了先河。
一战爆发后,德国战败,签署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导致经济崩溃和巨额债务。条约要求德国支付庞大赔款(约1320亿金马克,相当于当时德国GDP的数倍),为了偿还赔款和重建,当时的德国,也就是魏玛共和国,通过印钞(透过Reichsbank发行纸币),这直接引发恶性通货膨胀。
马克大幅贬值,你知道有多夸张吗?1923年通胀高峰时,物价每小时都在变,据说,有人去买面包,带了一篮筐的纸钞,结果不幸遇到贼,可笑的是,钱一分没少,篮子被人偷了。据说,当时物价每月上涨数百倍。
恶性通胀摧毁了社会保险基金。养老金、残疾保险和寡妇补助等依赖债券和储蓄,这些资产贬值到几乎为零。许多退休者一夜之间一无所有。
政府不得不介入,透过改革还加强国家角色,包括增加补贴和扩大福利,以弥补基金损失。1927年引入更慷慨的养老金、健康和失业保险方案,涵盖1700万工人,国家提供补贴如住房、公园和学校建设。
魏玛共和国扩大了俾斯麦体系,除了继续依赖雇主/雇员缴费,还增加了补贴,以填补通胀缺口。减少了对纯个人/雇主缴费的依赖,增加了国家统筹的部分。
而且,把失业险,住房,对单亲的母亲,以及残障人士都列入的福利保障的范围。
对社保制度推进的还有英国,1918年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政府承诺「适合英雄居住的国家」,也引入住房和失业救济。
两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各国大规模补偿战士,许多国家为退伍军人提供养老金、医疗和住房,以缓解战后矛盾。
尤其是二战后,各国从「战争国家」转向「福利国家」成为共识。德国模式透过国际劳工组织传播,影响北欧,如瑞典的「人民之家」模式)、法国1945年的社会保障体系、英国1942年建立NHS和全面福利。1935年,美国罗斯福新政借鉴德国养老金,实施社会保障法。意大利、荷兰等也采用德国式保险。受美国影响,日本1947年宪法引入福利原则,然后是韩国。
国际劳工组织在冷战与后殖民时期,推动全球推广,拉美国家如巴西1930年代养老金、亚洲的中国1951年建立劳动保险,受苏联影响,但间接也借鉴德国。90年代年,中国开始逐步建立和完善五险一金制度。基本上也是借鉴德国模式。
自此,德国模式「互动扩散」到100多个国家。
不过,现在全球的福利国家和社保养老体系,正面临老龄化和低生育率的挑战。
现收现付模式,就是年轻人交钱养老人。但现在全球生育率掉到1.6-1.8,远低于维持平衡的2.1。婴儿潮一代(1945-1965年生)现在大批退休,而且他们的寿命越来越长,平均超过80岁,所以领福利的时间拉得更长。
结果,缴费者和领钱者的比例,从过去的4:1滑到现在的2:1。
世界经济论坛(WEF)报告指出,养老基金缺口高达几万亿欧元,年轻人的负担会越来越重。美国的社会保障基金,2034年就可能耗尽。
全球对福利制度的推动,以及社会保障网的建立,让一些地方对福利依赖成风,导致人们不愿工作。像美国底层20%人口,劳动力参与率从1970年的70%掉到现在的36%,福利设计几乎在鼓励大家躺平吃福利。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曾警告:「政府试图透过福利来规划社会,终将导致个人自由的丧失和经济的低效。」
从南方国家来的移民,还喜欢去福利国家,他们对新国家的福利贡献少,却使用很多医疗和失业福利,造成资源紧张。这引发欧美反移民情绪高涨,右派声音得到支持,特朗普重返白宫就是典型例子。
要知道,这些欧美国家经济和财政压力本来就大。高债务、通胀、经济增长缓慢,让福利开销撑不住。发达国家福利支出占GDP 20-30%。美国债务超36万亿美元,其中很多因福利过大而起。英国养老医疗吃掉税收22%,最近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高涨,更凸显问题严重性。欧盟的法国、意大利福利造成的预算赤字过大,欧元规则还不让多借钱。经济慢下来还缺劳动力,尤其护理和制造业,但是要支付失业保险,财政负担更重了,如今福利从「安全网」变成「钱坑」。
西方国家政府试图把退休年龄提高到67-70岁、削减福利或加私人保险。但又遭左派政党阻挡。
到最后,央行只好扩大资产负债表,买进政府债务,这形同印钞,不可避免地导致货币贬值,稀释老百姓的储蓄。就像米塞斯所说:「通货膨胀不是自然灾害,而是政策选择的结果,它总是让富人得利、穷人受害。」各国央行不断买国债填补资金漏洞,表面上维持福利体系,但实际上透过隐形税收——通胀——转移财富。老百姓的储蓄和养老金购买力被稀释,生活成本上涨,却得不到相应调整。这不只侵蚀个人财富,还扭曲市场信号,阻碍真正经济成长,让整个体系更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