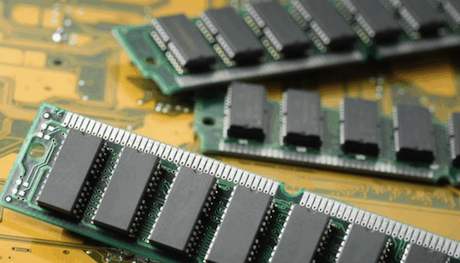“巴菲特指标”飙升到了218%,超过巴菲特口中所谓的“玩火”警戒线。传统解读很直接:股票市场比经济强得离谱,风险在积累,入场要小心。这样的直觉没错,但如果只靠这把老尺子来判断今天的市场,我们可能会既吓错,也错过真正的结构性信号。
先说清楚这把尺子量的是什么。巴菲特指标把股市总市值和一国一年产出的GDP放到一起,是一种宏观对照,原理简单而朴素。在工业化时代,这个比值能较好反映市场和实体经济的相对价值。但问题在于,今天的经济结构和三十年前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
科技公司的价值更多来自软件、平台、用户和网络效应,这些是无形资产,往往不直接反映在当年的产出数据里。公司可能把研发和用户增长当作资本化项目,而GDP仍以当期产出为核心,这就造成了分子和分母测量口径的不匹配。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现实是营收和利润的全球化。许多大公司的客户和收入来源不再以本国为界,全球化意味着美国上市公司的市值可以反映全球市场的预期,而美国的GDP只是本土经济的快照。把全球化的市值和局部的GDP硬对比,就像用一国的收入去衡量一家跨国集团的市值,它固然能发出信号,但信号里面混杂了统计口径差异和全球化溢价。
再者,金融化的力量也不能小看。过去十年低利率和宽松货币把资本成本压得很低,企业回购、杠杆收购和被动基金流入推高了估值。公司用较少的资本就能买回更多股份,这在数学上增加了每股盈利,进而支撑更高的市值。与此同时,投资渠道的变化也把更多家庭财富直接推向股市,交易成本下降和ETF的普及改变了市场的流动性特征。这些因素联合起来,使得市场的“价格”部分由宏观货币环境驱动,而非单纯由企业盈利支撑。
那么,218%是泡沫的证据吗?答案并不简单。部分行业确实存在泡沫性估值,这在高成长的科技和平台公司中更明显,它们的市销率和用户估值有时脱离了当下盈利基础。标普的市销率已升至高位,这说明市场越来越多地用收入而非利润来定价。这种情况在早期互联网泡沫时期也出现过,它最终以估值大幅回撤告终。但同样重要的是,技术创新带来的生产率跃升和新商业模式的出现,也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合理化更高的估值。关键在于区分真正的“范式变迁”与短期的投机性溢价。
这个指标的高值应该激发两种思考。第一是风险意识,市场广泛过热的信号要求更严格的仓位管理和流动性准备。第二是估值框架的更新,单一的市值比GDP已经不足以解释未来回报,必须把技术周期、竞争格局和现金流折现放在核心位置。换句话说,不是简单地“全部出场”或“全部持有”,而是要分辨哪里是真正的未来生产力,哪里只是短期情绪的堆积。
从政策和系统性风险角度看,巴菲特指标的上升同样提醒监管者和中央银行思考退出路径。长期的低利率会扭曲资产配置和风险定价,一旦货币紧缩到位,资产价格的重估可能来得迅猛而无情。这些都是指标本身无法告诉我们的,但却是市场回撤的催化因素。
因此我们需要对传统指标做两件事。第一,保留它的警示价值,把高比例看作配置调整的信号而非市场最后通牒。第二,发展新的度量方法,把无形资本、跨国收入和企业内生研发等要素纳入考量。理论上可以把GDP扩展为更广义的国民收入概念,也可以把市值与企业未来可收回现金流的折现进行更直接对比。无论方法如何演进,目标只是让“市值对经济”的比较更贴近现实,而不是继续用工业时代的尺子量数字经济的体温。
巴菲特指标并没有失灵,它在新的世界里仍然有用,但需要被重新解读。它的升高提醒我们市场的风险偏好已经显著提升,也提醒我们必须更新衡量工具和投资方式。真正稳健的应对是既承认估值的高度,也接受结构性变迁,做出更有层次和更有弹性的配置。这样,在任何一个未来到来时,我们既不被时代抛下,也不会在泡沫里做最后的赌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