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美国的第一次经济冲击发生在1999年至2007年间,那是中国从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阶段,也是数以千万计的农村劳动力和资本快速转移到城市工厂的历史时期。
巨大的变革引发了中国出口海啸式增长,物美价廉的商品对美国地方制造业形成了毁灭性影响。据统计,当时的中国制造抹掉了美国近四分之一的制造业岗位。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等城市——曾自诩为世界的运动衫和家具之都——成为中国1.9冲击的典型受害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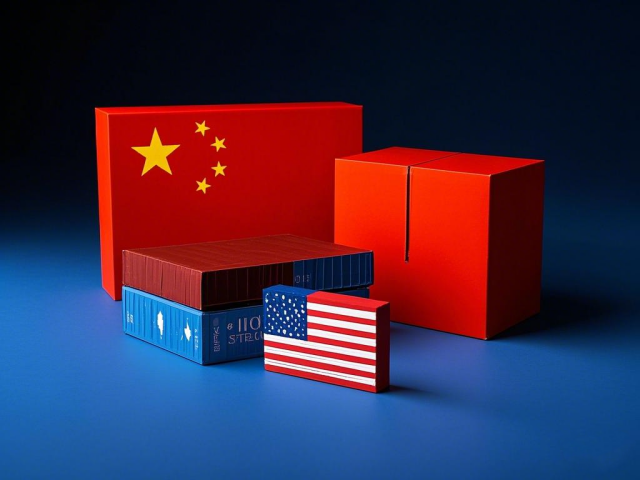
二十年过去,虽然这些地方重新开始增长,但新增的工作多集中在低薪行业。不仅是纺织、玩具、体育用品、电子、塑料和汽车零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遭受重创,美国整个中部和南部的产业结构都在中国1.0的冲击中土崩瓦解。
然而,当中国完成其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之后,从2015年开始,“中国1.0冲击”的能量开始快速衰退。此后,美国制造业就业经历了温和回升,在奥巴马政府末期、特朗普第一任期以及拜登执政初期均有所增长。
然而,现在的重点不是过去,美国即将面临“中国冲击2.0”的迎头撞击。而这一次的冲击,很可能比第一次更具破坏性。
如果说第一次冲击是中国终于做对了它早就应该做的事,那么第二次冲击则是中国从挑战者转变为领跑者。如今的“中国冲击2.0”,直接瞄准的是美国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高端创新领域:航空、人工智能、电信、微处理器、机器人、核聚变与核能、量子计算、生物科技与制药、太阳能与电池。
这是一个跨行业和全产业链的制造业挑战,美国的1300万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将和中国1亿个制造业就业者直球对决。两国巨大的体量差异将决定竞争格局。而谁掌握这些领域,谁就掌握了经济红利、高薪工作、技术标准制定权乃至军事战场主动权。
根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数据,在2017年,中国在多个尖端研究领域被引用最多,大幅领先于美国:电池领域占比超过美国70个百分点,AI算法和硬件加速器超过美国17%,光通信为37%,超导材料和磁体是14%,量子传感器27%,机器学习31%。
即使在美国领先的领域,比如量子计算,美国也只领先4个百分点(24%对20%)。而目前唯一有压倒优势的行业仅剩芯片设计与制造。
但如果将时间线拉长到2003-2007年,美国在-6-4-个前沿技术中曾领先60项,中国只有3项;而到2019-2023年,双方位置完全对调,中国领先57项,美国只剩7项。
这种翻转并非偶然。在90年代和千禧年初,中国主要依靠私企与跨国公司合作完成“世界工厂”的崛起。而如今的新模式,则是中国地方政府和私营企业协同发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布局。
安徽合肥,这个曾默默无闻的内陆省会城市,在五年内成为中国第二大电动车生产地。原因在于政府敢于下注风险投资,支持陷入困境的电动车企业,并在本地推动研发体系建设。
结果是,包括比亚迪(BYD)、宁德时代(CATL)、大疆(DJI)、隆基绿能(LONGi)等全球领先的新兴企业均在中国土壤中诞生,且多数不超过三十年历史。
这些企业的成功并非北京的一纸命令的结果,而是源于残酷竞争的产业政策与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相比之下,西方国家甚至误解了中国政策的本质,仍把这些核心决策误读成类似欧盟支持空中客车——传统的国企扶持模式。事实上,今天各国上空盘旋的大疆无人机,比任何一个西方对中国政策的误判更能说明问题。
中国冲击1.0的动力终结于低成本劳动力枯竭,而2.0版本却无需依赖劳动力红利。即使中国在服装和家具等产业开始被越南赶超,中小企业倒闭和失业率攀升的情况下,它也没有回头看。
北京的决策清晰而坚定的聚焦于二十一世纪的关键科技领域。只要中国拥有资源、耐心和纪律,这场新冲击将持续下去。
而美国的回应呢?主要且唯一的就是关税——不是仅中国,而是对所有国家,所有商品,全面加征。这不仅是对20年前失去的贸易战的落后反应,而且无法为未来铺路。
讽刺的是,照此发展,美国或许真的能拿回那些制作运动鞋的岗位。甚至,到2030年我们可能会在德州组装 iPhone——这项工作曾被讽刺媒体调侃为“连中国工人都盼望早日被机器替代的岗位”。
不过特朗普真的想让美国重回荣光,再次成为制造业的热土,关税永远不会是答案。它可以是工具,谨慎且精准,而非全面开火。那个曾经信奉自由贸易的美国,如今不再如此。美国在中国冲击1.0中表现出的无序和懈怠一直都在,现在,它将面对2.0时代的迎头痛击。
没有哪个国家能主宰某些产业的兴衰命运,但却可以决定下一轮产业革命在哪片土地上发生。如今,美国试图凭借芯片和关税这两张仅存的王牌主导未来,还沉迷于重返“黄金时代”的幻觉,这种路径依赖只会让它在下一个十年彻底丧失全球领导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