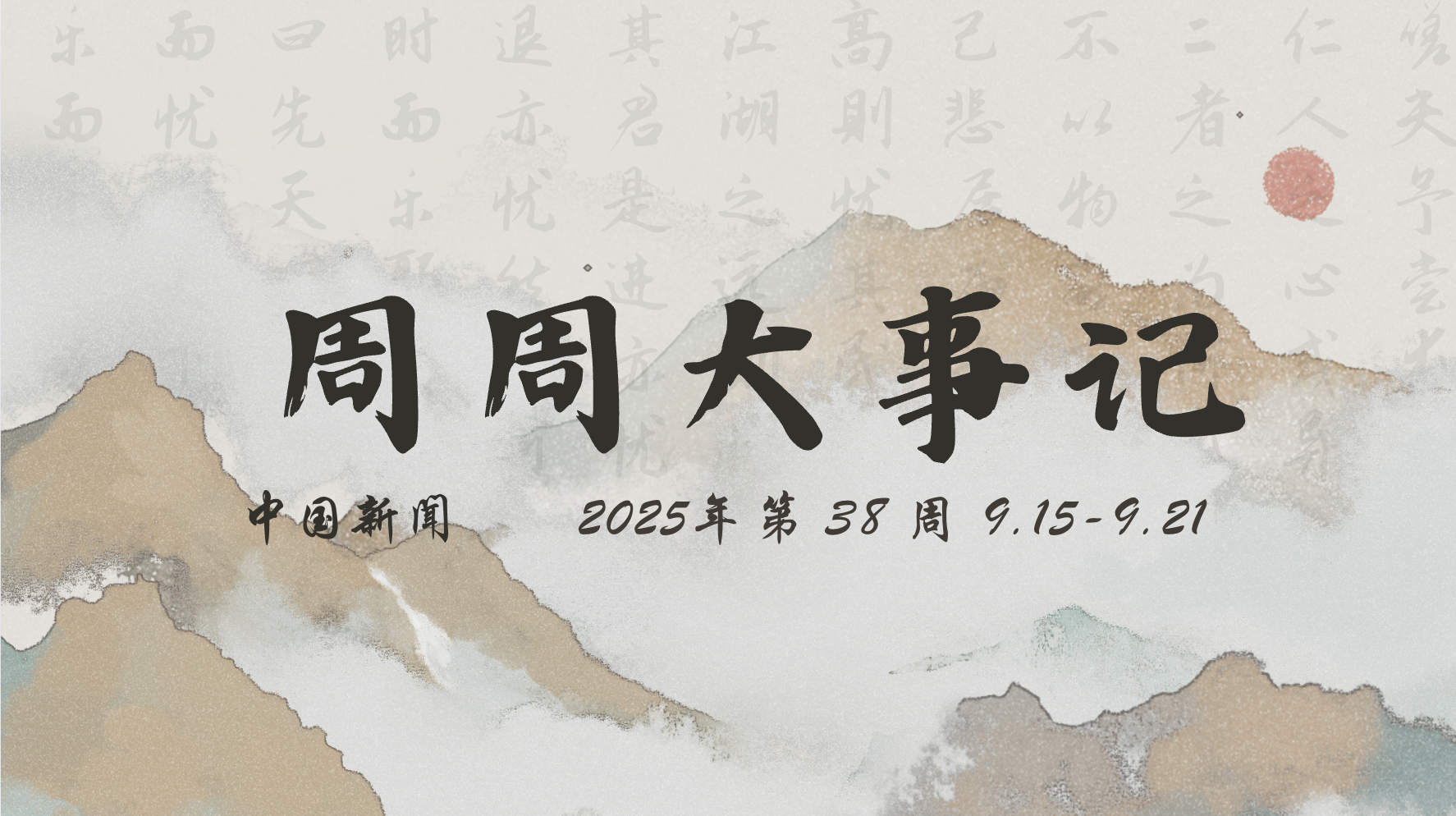当美联储在2025年9月如预期降息25个基点时,市场将其视作宽松周期开启的信号。投资者迅速计价年底前再降两次的可能性,仿佛货币政策的走向已成定局。然而,在看似确定的表象之下,一场关于未来路径的根本性分歧正在决策层内部悄然成型。这一次降息,与其说是新一轮宽松的起点,不如说是一次试探性的折中——它既回应了市场压力,也保留了政策回旋的余地。而更大的可能性是,这已是美联储在2025年能做出的最后一次降息。
支撑市场乐观预期的,是点阵图中位数所暗示的“两次额外降息”。但若穿透这一聚合数据,便会发现其背后并非共识,而是一场结构性的分裂。19位FOMC成员中,有9人支持年内再降两次,6人则认为本次降息已是终点,另有两人仅支持再降一次。更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两个极端预测:一个主张追加125个基点的宽松,另一个则干脆反对本次行动。这种分布不是偶然,而是反映了决策层对经济基本面判断的根本性差异。
分歧的本质,不在于对通胀的解读——双方都承认当前物价压力部分源于关税带来的供给冲击,也都倾向于将其视为暂时性因素——而在于对劳动力市场的叙事权争夺。鸽派认为,就业市场正“接近停滞速度”,前期数据的疲软足以构成预防性降息的理由。他们担忧,若等到失业率明显攀升再行动,可能为时已晚。这种思维延续了美联储近年来“宁可早不可晚”的风险管理逻辑,尤其在疫情后经济波动加剧的背景下,预防性降息被视为避免硬着陆的必要工具。
但另一派则提出了更具结构性的视角:当前劳动力市场的“疲软”,可能并非需求萎缩的信号,而是供给受限的结果。移民政策收紧、驱逐出境增加以及非公民群体中的不安情绪,正在抑制劳动力供应。企业招聘意愿未减,但可雇佣的工人变少,导致就业增长放缓。芝加哥联储行长古尔斯比强调应关注比率而非绝对人数,正是出于这一判断。若此成立,则就业数据的走弱并不意味着经济衰退迫近,而更像是一种“供不应求”的结构性错配。
这一判断的政策含义极为关键:若疲软源于供给端,降息不仅无效,反而可能加剧通胀压力。货币政策擅长刺激需求,却无法解决劳动力供给的制度性障碍。在这一逻辑下,9月的降息更像是一种政治与技术妥协——既回应了市场对宽松的渴求,又未彻底放弃政策克制。而后续是否继续降息,将高度依赖劳动力市场是否出现真正的恶化信号,而非单一数据的短期波动。
事实上,近期多项指标显示出经济动能的回归。8月零售销售连续第三个月增长,实际消费在经历上半年停滞之后重拾扩张势头。亚特兰大联储的GDPNow模型显示,第三季度GDP年化增速有望达到3.3%。尽管该模型存在误差风险,但在后疫情时代预测能力普遍下降的背景下,其持续指向正增长,仍具参考价值。股市处于历史高位,财富效应为消费提供支撑,这些都与“经济即将衰退”的叙事形成张力。
或许,美国经济的确曾因“解放日”关税政策引发的不确定性而短暂放缓,但企业与消费者已逐步适应新环境,经济展现出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政策制定者若仅依据过去几个季度的疲软数据继续降息,无异于用过去的地图导航今天的路况,极易导致政策过度反应。而一旦通胀因宽松政策再度抬头,美联储将陷入更被动的局面。

因此,点阵图中那6位认为“本次降息已足够”的决策者,并非保守或滞后,而是试图在数据滞后性与政策前瞻性之间寻找平衡。他们所依赖的,不是单一指标的瞬时读数,而是对经济结构变化的深层理解。他们的立场,本质上是对“数据依赖”原则的更高级应用:不是被动跟随数据,而是识别数据背后的驱动力,并判断其可持续性。
然而,货币政策从未在真空中运行。政治压力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渗透进决策过程。特朗普持续公开呼吁大幅降息,攻击鲍威尔的独立性,并试图通过司法手段罢免持异议的美联储理事库克。尽管库克在上诉法院胜诉,但案件已提交至最高法院,其最终结果将直接挑战美联储的制度独立性。在这种环境下,FOMC成员即便秉持技术官僚立场,也难以完全屏蔽外部噪音。
政治影响可能以隐性方式作用于决策:一部分人因担忧报复而倾向鸽派,另一部分人则因捍卫制度而坚持审慎。这种心理博弈虽不直接改变投票结果,却可能加剧内部分歧,使政策路径更加模糊。而模糊本身,就是一种信号——它表明美联储正在努力在数据、市场预期与政治压力之间维持脆弱平衡。
最终,2025年的货币政策可能走向一个看似矛盾的结局:一次降息之后,长期按兵不动。这不是因为经济强劲到无需支持,也不是因为通胀失控必须紧缩,而是因为当前的疲软更多是结构性而非周期性的,降息的边际效用正在下降。市场期待的“预防性宽松”,在供给约束和政治不确定的双重背景下,变得愈发谨慎。
这标志着美联储政策逻辑的深层转变:从应对周期波动,转向管理结构性失衡与制度风险。降息不再只是对失业率或通胀的简单回应,而是对经济韧性、政策独立性与长期信誉的综合权衡。9月的这次行动,或许正是这一新范式的开端——它不是宽松浪潮的起点,而是一次临界点上的试探。能否守住克制,将决定未来几年货币政策的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