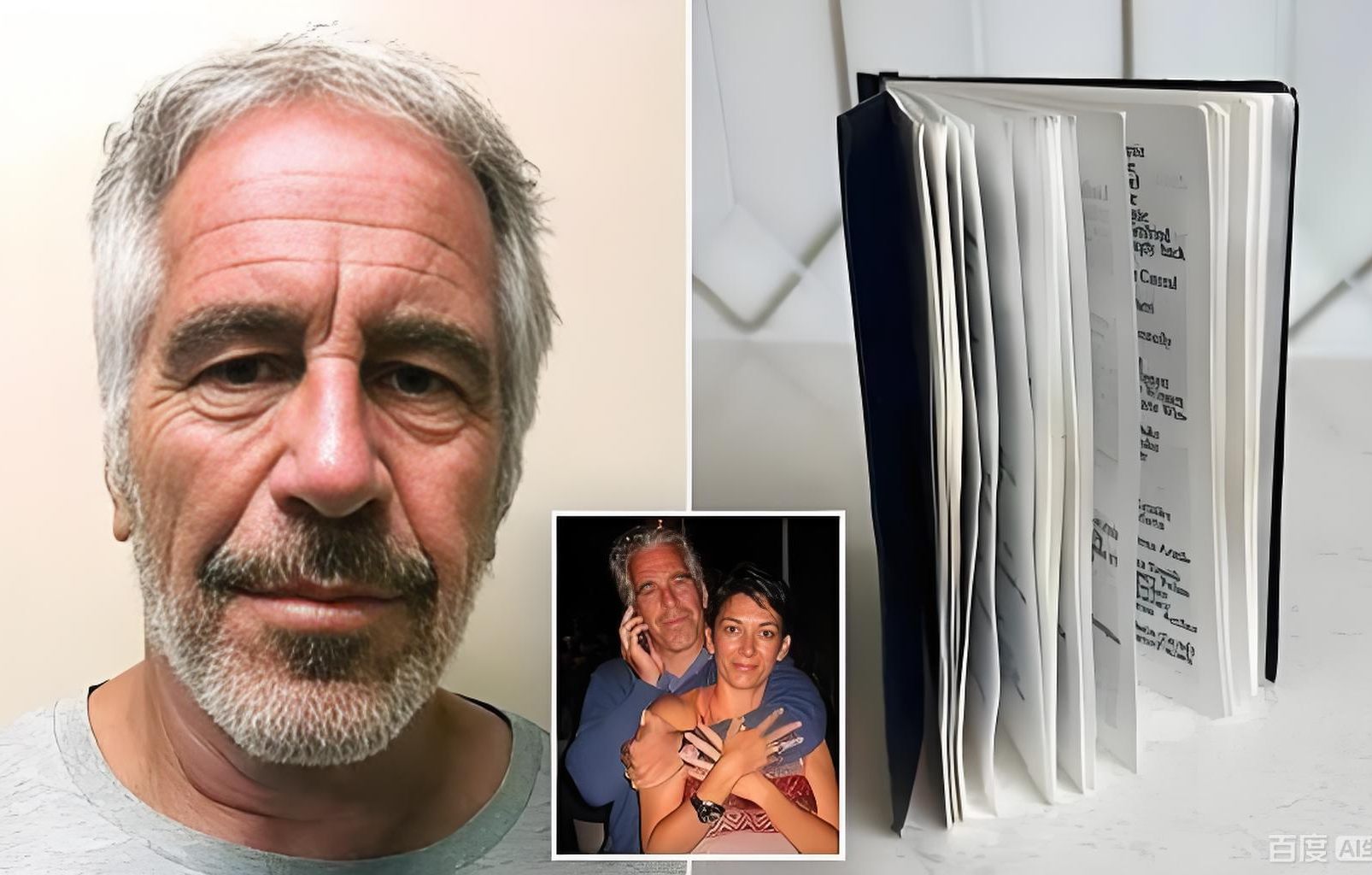2025年7月6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再度发出关税威胁,称可能对金砖国家加征10%的额外关税。这一表态表面上是冲着中国而来,但更深层次所反映的是特朗普政府对“全球南方”的不安。
十七年前还被高盛当作一个“投资概念”的金砖国家,如今已成为现实中的地缘政治力量集合,而这有可能成为改写全球秩序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2024年,金砖五国——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在全球 GDP 中所占份额已超过了32%,而加入申请国的名单还在不断拉长。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指出,西方若希望遏制跨国企业、真正重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就必须认真对待并参与金砖国家的机制,而不是一味打压或漠视。因为无论从供应链、价值链和经济网络都绕不开金砖国家的深度参与。
金砖机制的影响力崛起并非偶然,而是在多重结构性矛盾激化背景下的自然产物。以加沙战争为例,在南方世界看来,这场冲突加剧了全球“南北分裂”的认知。以色列对加沙的猛烈轰炸造成数千名平民死亡,而二十年前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也带来了数万计的平民伤亡。
这一“选择性正义”的外交双标已成为南方国家长期的不满来源。尤其是在穆斯林世界之外,越来越多的南方国家对西方的“价值输出”产生质疑,金砖因此被视为一个更可控、更平衡的替代性平台。
自2009年成立以来,金砖机制在2011年确定为五国组合,并于2014年成立了金砖新开发银行,总部设在上海。虽然目前规模仍小,但未来仍有动能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挑战,尤其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拒绝改革投票权结构、持续边缘化发展中国家的前提下。
2023年8月,在约翰内斯堡的峰会上,金砖宣布将在2024年起接纳六个新成员——沙特、阿根廷、埃及、阿联酋、埃塞俄比亚和伊朗。这六国是从四十余个申请国中遴选出的,显示出金砖机制作为“全球中产阵营”的吸引力。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预计到今年年底,金砖十国的 GDP 总额将超过45万亿欧元,占全球总量的40%以上,而 G7 国家的总GDP则维持在30万亿欧元左右。
尽管从人均月收入看,金砖国家仍明显落后——不到1000欧元,而 G7 国家接近3000欧元——但考虑到金砖成员国的人口占全球人口的近45%,这一差距并不会削弱其整体运作,反而凸显出这个新兴经济体未来巨大的增长潜力和发展空间。
当然,金砖内部的问题也非常多。其中,政治经济制度的巨大差异或将掣肘这个新兴经济体。比如,如中国的“数字经济独大”、俄罗斯的“军政寡头体系”并不具备普遍吸引力,但这种松散结构反而让成员国在没有经济强权的压力下且彼此不干涉的基础上更加从容地推进合作。
而其他的较大的金砖成员国家,像印度、巴西。虽然被认为在金砖机制中缺乏协同和共性力,而且最近几年也遭遇到了较大的困难。但并不一定是西方观察到的那么严重。
以印度为例,其选民数量超过所有西方国家的总和,2019年大选的投票率达到67%。这表示印度的经济情况有明显改善,也是对莫迪新的经济外交平衡政策的认可。
反观西方国家,2022年法国全国选举的投票率仅为48%,且贫困选区的参与度暴跌,这是200年来前所未见的现象。
美国的民主制度近年来也频频暴露脆弱性,从关塔那摩监狱问题,到国会山暴动,再到以关税为武器和美国优先的“特朗普主义”追随者,叠加全球通胀和价值双标。西方的“制度输出”正在失去道德说服力。这为金砖持续且稳步的推进提供了腾挪的空间和生存的土壤。
G7 和西方国家的问题是,一边高举民主与人权旗帜,另一边却摆出“教训全世界”的姿态。同时他们还甘愿与最腐败或最暴力的政权合作,因为能从中牟利。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拒绝改变旧世界的规则,拒绝在权力与财富分配机制上进行结构性变革。
而西方国家的独断与傲慢损害了像联合国、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公信力。导致新的经济秩序的结构改革长期被拖延,甚至搁置,包括金融与税收体系的重塑。还有设立对全球最富有的主体(跨国企业与亿万富豪)征收最低税率的机制;按人口与气候脆弱性在各国间重新分配收入。
目前的全球最低税政策覆盖范围过窄,税率过低,执行上漏洞百出,且绝大部分收益流向北方富国。而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无疑会让整个世界陷入新的金融动荡。
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已经开始反感这个曾经给西方世界带来繁荣的陈旧的经济秩序,并质疑其存在的价值。尽管这些反抗的声音目前只是来自四面八方,微小和无力,却仍被越来越多的人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