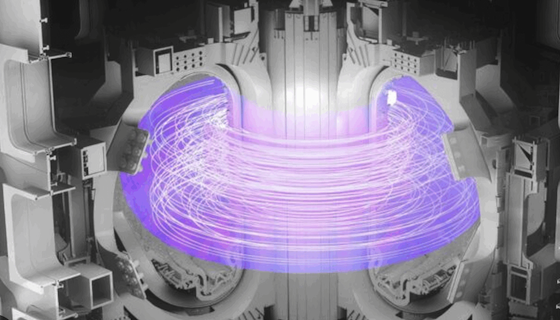新加坡乌节路地铁站的Manus招聘广告在阳光下格外刺眼,而北京中关村的办公室里,最后几名员工正默默清空工位。四个月前被誉为“下一个DeepSeek”的AI新贵,以近乎决绝的姿态完成了自我切割——清空微博小红书、屏蔽中国IP访问、解散120人本土团队。
当创始人肖弘站在新加坡SuperAI大会的聚光灯下宣告总部落地时,北京蝴蝶效应科技的员工正在签署离职协议。这家曾将邀请码炒至9万元天价、月活突破2000万的明星企业,在五个月内经历了断崖式坠落:五月用户量腰斩至约1000万,定价199美元的Pro版终究没能挽回颓势。
撤离行动早有预兆。五月起,肖弘与联合创始人陆续迁居新加坡,加州圣马特奥与东京的办公室同步设立。六月中旬,新加坡公交站台已被Manus的招聘海报覆盖,首席产品官张涛在SuperAI大会上正式确认总部易主。
七月这场撤离达到高潮:仅有40名核心成员获得前往新加坡的机会,其余80名员工带着N+3或2N的补偿离开——这远高于中国法定标准。与此同时,新加坡招聘全面启动,当地平台MyCareersFuture显示,AI工程师月薪标价8000至16000美元,折合人民币高达13万,触及狮城顶尖薪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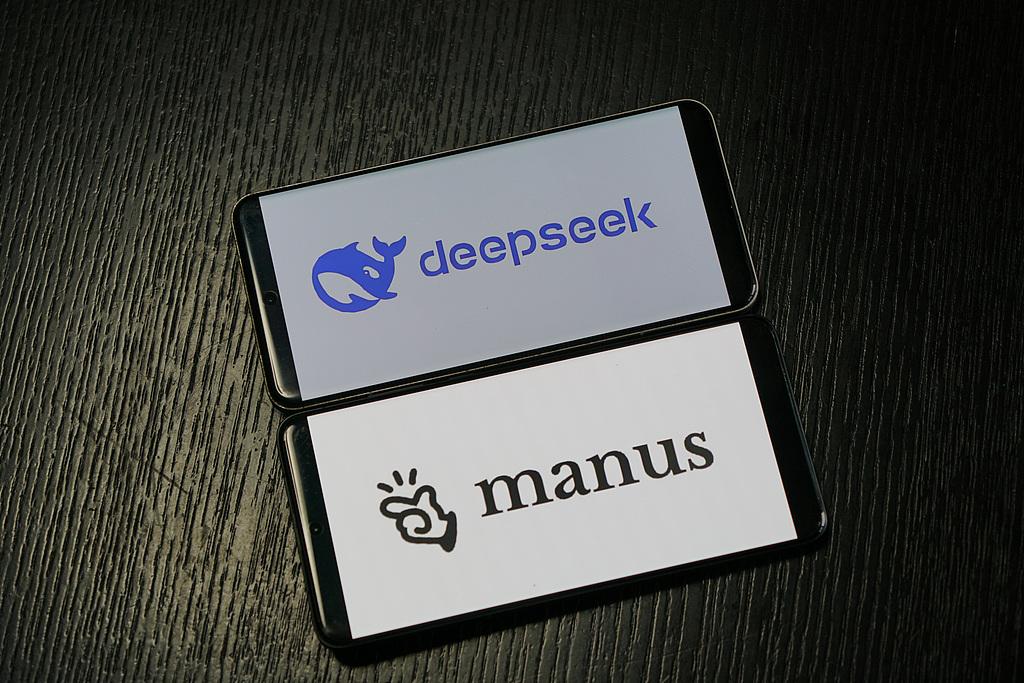
更沉重的枷锁来自政策层面。美国财政部对Benchmark领投的7500万美元B轮融资启动审查,这笔曾让Manus估值飙升至5亿美元的资金,如今成为悬顶之剑。依据2025年生效的《对外投资安全计划》,美资注入中国AI企业需申报国家安全风险。
为突破资本困局,Manus紧急启用2023年注册的新加坡主体,构建起“开曼-新加坡”三级控股架构。这种设计虽可借新加坡与中美的双边税收协定降低成本,却意味着彻底斩断中国市场的运营根基。
技术限制同样致命。美国升级对华芯片管制后,英伟达特供芯片H20/L20全面断供。依赖多模型协同的Manus陷入算力困境,与阿里合作开发中文版的计划随之流产。颇具讽刺的是,当中国用户打开官网只能看到“该地区服务不可用”的提示时,国际版产品仍在持续迭代——从美国线下沙龙到东京开发者大会,其战略重心始终在海外市场。
“如果证明中国出生的创始人能在新环境做好全球化产品,那就太好了。”肖弘在社交媒体的感慨,揭示出这位曾拒绝搬离武汉的创始人的艰难转身。本土市场承载着技术理想,但全球竞争需要中立跳板。
当资本合规与算力获取成为生死线,选择变得异常残酷。市场反应更印证转型代价:开放注册后用户量持续下滑,Pro版高价策略未达预期。第三方监测显示,竞品GenSpark上线45天即创收3600万美元,而Manus同期收入仅936万美元。更深隐患在于新加坡三倍于中国的人力成本,在尚未盈利的背景下,这笔开支正持续吞噬融资储备。
当120人的中国团队缩减为新加坡滨海湾写字楼里的40个工位,这场撤退已超越商业选择本身。”三级架构是技术全球化的无奈妥协,也是地缘变局中科技公司的生存样本。当技术理想遭遇地缘政治,远走他乡有时不是终点,而是新一轮生存竞赛的起点。